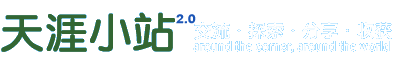无常中的永恒---献给做书人严喆民(1960年2月29日-2008年12月10日)
时间真快,她去世已经一年了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春末,在北加州的山中,我们寻找着艺文印书馆严喆民编辑的住处。停车、问路、打电话,弯过几条窄巷,爬上几道小坡,我看见了喆民,她站在一缕和熙的阳光下。
虽因<<时间简史>>中文繁体版结缘十几年,我们却从未谋面。我隐约知道她有残疾,但一直以为那不过是很轻的残疾。在很多次通话中,她的风趣常让我大笑。看到她时,我还是笑着,但心却沉了下去。我绝想不到她是这么瘦小,其身高只及我胸,而我已算矮个。我上前拥抱她,感念颇多,却不敢用力,她身体的脆弱远在意料之外。事后,我先生也说绝没想到她的残疾是这么严重。
喆民将我们让进客厅。茶几上,摆着切好的橙子和凤梨酥。靠窗垂着一副条幅,“学浅自知能事少,礼疏常觉慢人多” 。细看题字人,原来是一代考古宗师董作宾。另一面墙上挂着鲁迅弟子台静农的墨宝。壁炉前搁着一张木凳儿,简单别致。她笑说:“那是小弟从沙特阿拉伯带回的骆驼鞍子。”
松阴遮蔽,室内微暗,几案上坐着一盏灯,散发着宁静的光。微黄的灯罩是透明胶片做成的,图案展示着<<清明上河图>>,似在追怀故人旧事。我欣赏着灯罩,她又一指对面:“那边还有一个。” 回首望去,那个灯罩上绘着竹兰梅菊。她说:“这两个灯罩都是董作宾先生的公子送的。他是摄影师,在暗房里冲洗出胶片,他太太再把胶片固定在铁架上,很费时费工。当年他们夫妻做了一两百个这样的灯罩,被台湾文化界的人一抢而空。他们赶快送了两个给我父亲,要不就没有了。”
她的父亲严一萍先生是董作宾的弟子,也是知名甲骨文考古学家,其著述包括<<甲骨学>>,<<甲骨缀合新编>>,卜辞书法“造型别致,用笔颇高”( 注一)。2003年,在西安的秦俑博物馆里,我看到了董作宾和她父亲的合影。
我们谈起她过世的父亲,她回忆道:“小时候过年,别人家放鞭炮,人来人往,非常热闹。自己家却冷冷清清,因为父亲不许拜年,也不许放鞭炮。父亲说,平时杂务缠身,只有过年才得以清静,可以写大段文章了。”她又说:“你的先生若换个研究题目,再加些旧学的功底,更老派些,那就是我的父亲。”噢,是那种生活在自己的研究世界中,不大近人情的学问人。
她父亲的书房紧邻客厅。房间的正面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,像中之人儒雅清隽。四壁皆为檀木书架,满架整齐地堆放着线装书,其中的若干还夹着纸条,书房的主人似乎无时不在研读。打开其中的一卷,一枝芸草掉了下来,拾起一闻,清香依在。到台湾之后,她的父亲不愿开口求人去谋一教职,而自己撰写的著述又无处发表。于是,在董作宾的鼓励下,干脆自己印书。董先生望重士林,书局也曾延聘董先生为发行人。
我坐在“驼鞍”上,她道:“我读了你的许多文章,那些写旅行的.....。”还没说完,眼圈儿就红了。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,不知说什么才好。这样一个好奇活泼,聪慧善感,生命力极强的女子,多想走得远些,再远些,去看看世界,但是却不能够。
她天生脊椎弯曲,残疾伴随终生。十岁那年,她曾动过一次大手术。术后整整一年,她从脖子到骨盆都需要绷上石膏衣。在挥汗如雨的溽暑,那该是怎样的煎熬和监禁。身上疼痛,脾气自然也不会好,上中学以前,除了照顾她的生活,家人还得百般容忍这个小‘暴君’。
十二岁时,她考入台北的卫理女子中学。因为需要住宿,她父亲无法确定学校是否愿意接受她。于是他拉着她的手,带她去面试。幸亏校长陈纪彝非常开明,同意让她‘试一试’ 。这一‘试’就试到了毕业。
在学校里,她第一次折被铺床,自己事情自己做。虽然她一直是最矮小的,走路也最慢,但从未因身体缺陷而受到嘲笑。学校举行舞蹈比赛,为了让她也能参加,编舞的同学特意编排了一个不动的圆心。体育课考试,为了让她能够通过,同学们压住她的腿,抬起她的上身,终于完成了五个仰卧起坐。
她是幸运的!在人格成长最重要的那几年,她自省向上,师长和同学又心地淳厚。然而,她也是不幸的,支撑身体的骨头却始终未能随着智慧和人格一起成长。待年纪再长,她的心肺更得加倍工作,才能供给生命的氧气。
我问她:“小时候,你是否会因与他人不同而感觉不便?”她说,“噢,我从小就已经很老了。很小的时候,我就想,既然无法改变,想也没有用啊。我从来没有试过其他人的身体,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,那是一个我熟悉的世界。唯一能提醒我的是一些特别恶劣的人,上下打量我的目光。”
她熟悉的世界是一个书的世界。迄今,她父亲创办的艺文印书馆已超过半个世纪,年长她8岁。除了印自己的书,她的父亲还具有版本学独到的眼光,他精选影印了故宫的刻本古书。1950年代的台湾,典籍极为缺乏。当书局出版了「阮刻十三經」,学人竟为该书的出版而”欣喜若狂“。
她父亲对前来购书的学生们说:“读书要用功,识字最重要!当然更要讲求版本好的书。”張之洞也讲过类似的话:“读书不知要领,劳而无功,知某书宜读,而不得精校精注本,事半功倍。” (注二) 据她回忆,每出一本书,父亲都要看校样十七次。
1958年-1966年间,据台湾国家图书馆(当时为中央图书馆) 国学书目统计,台湾影印重印以及重新整理的古籍大约715种,她父亲的印书馆则占58种,仅次于世界书局。尽管如此,在这喧嚣功利的世界上,这是一间冷僻的书局,50年前是,今天仍如是。
喆民大学毕业后,曾短期出外做事。后来父亲的书局需要人手,她就顺理成章地做了封面设计和文字编辑。所幸在这家的孩子中,她对历史最有兴趣,国文功底深厚,个性机智沉稳,进退有据。自1987年严一萍先生逝世之后,所印之书主要由她编辑设计。
望着那盏<<清明上河图>>的台灯,喆民忆起艺文的旧事。很多年前,一位读者对她说,那边有家书店卖同样的书,只是版本小一些,卖得很便宜。 于是她就去‘那边’ 看一看 。果然那些书不但文字一样,连封底的版权字样都照抄无误,唯一的不同是在原封面上加印了一个封面,在大陆印刷。
她告诉店主这是违反版权法,必须从书架上取下。岂知那店主非但不听,还伙同自己的父亲打上门来,拍着桌子大闹。
“当时出版社只有我和公司小妹二人。他们大概骂了4-50分钟。我一直没说话。我看那老人满脸通红,担心他中风或昏倒,就叫小妹守在电话机旁,一旦发病,立刻叫救护车。…”
大约五年前,我们很久没有她的消息。几次致电,均无人应答。后来才知道,她进出于急救室和加护间有数月。她指着脖子上隐约可见的疤痕:“你看这就是气管切开的地方。他们缝合得很好。”我说:“霍金教授也做过气管切开手术。我上次去见他,看到他脖子上有个洞…。” “那是自然愈合,我的体质太弱,无法自然愈合,只好缝合。”她因此又做过两次手术,她这辈子大概做过5-6次手术。那次手术之后,她无法和母亲一起回台湾了。
她又笑笑说,“我难过的时候,就想到霍金教授。至少,我还可以自己走出这间屋子,还能说话,还能开车去做复健。”
“你自己开车去?”
“是呀,做大约1小时的复健。再剩点气力开回来。不过每次一到家,就没力气站起来了。”
出生不久,她就做了上顎縫合手术,外表看不出來,但口腔里却少了小舌。对她来说,G、K、J等都是高難度的发音。她自嘲道:“通常累了,那些难发的音,我就打馬虎眼了。”
虽然她咬字有些不清,但丝毫不影响她的谈兴。“那天我躺在急救室,听到一个男孩子大喊大叫。我看不见他,只能隔着帘子听,似乎还是斯坦福的学生。 那男孩坚决要求出院,一直在和护士吵闹,英语说得非常标准。后来,护士叫来心理医生。心理医生对他说,你看你这么冲动,出去一定会伤害他人。现在我就给你开镇定剂,你必须吃下去,72小时之内不得离开。这男孩一听,就冲向门口,医护警卫一拥而上。后来,他又说要打电话。突然,我听到了台湾国语---拜托你们,快想想办法,把我从这里弄出去。我还有三门终考,如果出不去,我就死定了…”。她维妙维肖地模仿着,流利地转换于中英文中,这淘气的女子逗得我们哈哈大笑。
她喜欢调侃,调侃医院,调侃自己,那调侃带着苦涩:“早晨刚醒,护士就进来了,笑容灿烂地问你怎么样啊。唉,经过了一个长夜,一个努力地积蓄力量和死神搏斗的长夜,笑一下都要加倍努力,我实在笑不出来。护士一看,马上紧张起来,要不要去叫心理医生…?” “当然啦,比起弟弟妹妹,我父母对我照顾的更多些。就像一窝猫,老猫对那只缺手缺脚的,自然就舔得多些。”
据她回忆,当时她的肺功能只剩下15%,病危通知已下,就在命若游丝的瞬间,她突然回醒过来。冥冥之中,一个白色影子站在她面前,一字一顿地问道,“Do you want to live? ” 她不加思索地点点头,然后,就在一张纸上胡乱地划了几道。于是,凭着那张‘同意活命’ 的字据,为了一线可能的生机,医生切开了她的气管。其后数月,各种管子针头伴随着她,插管、拔管、发炎、吸痰。时过四年,她依然无法完全离开呼吸器。
呼吸原本是一个自然的过程,几乎感觉不到。一旦感觉到,要努力地呼吸,就非常难过了。我曾有过呼吸障碍,呼吸困难的时候,起坐不是,并尽力去忘却呼吸。此时呼吸虽然困难,头脑却非常清醒,清醒得让人恐惧,人不能总徘徊于生死之间。然而,当活下去变得万分艰难,要用尽所有的气力,我不知道是否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
她是一个做书的人,为了感谢我的访问,她特意为我做了一本书,那可是真正的手制珍本。
我打开包书的绵纸,封面洒落着褐色的麦粒,缎带飘着紫色的蝴蝶。在麦粒和蝴蝶之间,一行字显现出来 :“聚散无常” ! 我哭了。只有她这样命悬游丝,悟透生死的人才真正知道何为‘无常’啊。
这是一本薄薄的小书,序言、跋文和目录却样样俱全。在前言里,她写道:“喜欢用手工做独一无二的珍本书,送给爱书爱文字的人。感谢远客来访,以此薄薄的小书为念。”
在跋文中,她写道:“眼睁睁地,慢慢地道别。时间多凌迟…..叮咛一声,小心走好,将来再相见,我们别道别。”
人间岂止聚散无常!几千年来,人们就意识到这一点,他们卜年,卜雨,卜禾。她自幼残疾,成年多病,更邻近无常。然而,无常却令她与无聊、喧嚣、功利甚至爱情绝缘,她生命的每一刻都非常宝贵,只能将旦夕的生命投入到永恒的追求中。
殷墟的甲骨上留下了古人的卜辞,她父亲的一生就和甲骨文作伴,这些古老的文字也一直牵连着她的生命。在这太热闹的世界上,看似耀眼的事体何其多也,却未必敌得过二分尘土,一分流水。冷僻的甲骨文,她脆弱的生命犹如微火,虽暗,却总是一息尚存。这微弱的薪火传承着,岁岁年年。
杜欣欣写于2005年5月
改于2008年12月14日(注三)
注一:柳学智:甲骨文与甲骨书法
注二:黃端阳:沧海何处寄萍踪——严一萍先生与艺文印书馆
注三:应严喆民知友要求,此文在她生前不发表。